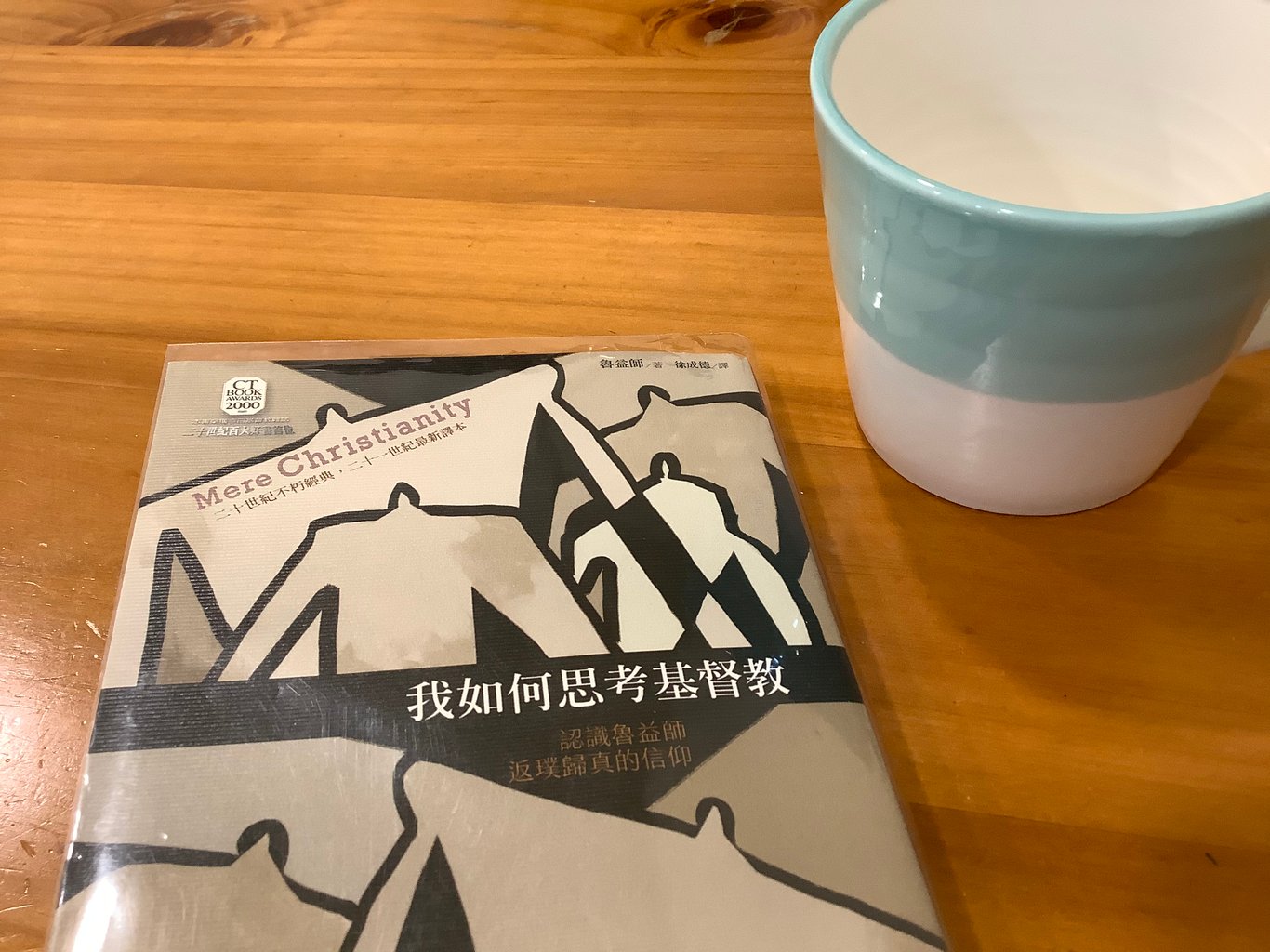十七世紀一個荷蘭士兵與平埔族女孩的愛情故事(四)
"誰是基督從各地集合起來的人?
只有那些神揀選為祂的孩子,以後要帶到天堂去的人。"
"請告訴我,神是否也揀選你?"
是的,我是神的孩子。"
她在那裡,在草棚搭起的教室的角落,專心的在紙上抄寫教義問答。范勃亨一眼就在教室的人群裏望見她。她黝黑的眼珠如此專注、美麗,一不小心,范勃亨發現自己呆呆地凝視她。
旁邊的平埔族女孩,結婚的與還沒有結婚的,有不同的衣服和髮飾,她們發現范勃亨的視線,戲鬧的用手肘輕推Tagutel。
[看,是你的丈夫。]
Tagutel鴿子一般的眼睛抬起頭來看見他。她的臉一下子紅了。丈夫在白日來探訪妻子是不符合習俗的。她低下頭去,假裝沒看見他。
"如果你現在很努力很熱心地以基督之名向神求告,你的心會變得如朝露般清新嗎?
是的,一定會變的很清新。"
"誰給你這種感覺?
聖靈使我們的心靈清新,就像渴者有水喝一樣。"
他等著她從教會學校下課。然後一起散步回她的家。十月傍晚的風十分沁涼。
「你今天怎麼會來?」
「妳知道我現在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了。」他靦腆的笑。
她有點憂傷的點頭。如果不是因為她,范勃亨在公司中的職務原本如日中天,不會瞬間遭到冷凍。
「今天在學校的學習如何?」他轉變話題。他覺得很有趣,Tagutel居然會想重新回到學校。她說:「我想更認識祂。」
Tagutel板起臉孔,突然轉變成荷蘭老師歪扭的新港語腔:「誰會是法官?」
范勃亨歪著頭想了想:「是耶穌。」
「他要審判什麼?」
范勃亨笑著搖搖頭。
Tagutel一本正經地念誦答案:「祂將審判我們所做的,所說的,所想的。」
他們一起大笑起來。范勃亨感到心頭哽住的一塊石頭,那些無法為自己辯解的委屈,似乎也隨著兩個人的笑聲一掃而空。
「今天我來,有一件重要的事。」范勃亨熱切地拉住Tagutel的手。
「妳知道,我現在沒有工作了,但是,我可以幫妳種田,我願意用我的所有力量保護妳,一輩子。」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戒指,那是離婚時他唯一要求歸還的禮物,是他母親遺留給他的家族寶物。
他單膝跪下。「我之前沒有這麼做過,因為這不是你們的習俗。但是我現在想要這麼做,因為我希望這是很正式的。我希望在神的面前和妳重訂婚約。」他把戒指套在她的手上。
Tagutel驚訝地說不出話來,她有些憂心:「牧師不會同意我們這麼做的。」
Tagutel說的沒錯,牧師不會同意為他們證婚,因為在牧師的眼裡,Tagutel是有罪、汙穢的,不能穿新娘子潔白的白袍。對他來說,他們的婚姻已經死了,埋進墳墓裡,不可能復活。
范勃亨用力地握住Tagutel的手。「沒關係,但是我們還是會重新舉辦婚禮,比第一次更盛大。因為現在我更愛妳了。現在我更知道怎麼許下約定........我永遠不會再放開妳的手。」
Tagutel的眼淚從眼眶裡奔瀉而出。在此刻,她知道自己是被揀選,而且被愛的。
未來仍然有許多令人充滿不安,旱季持續著,附近山村的村落傳出正打仗的風聲。還有如果得罪荷蘭人,他們要怎麼在新港社生活下去呢?
但是她願意將自己的生命放在這個人手中。她有這樣不知從何而來的信心。
范勃亨與Tagutel再婚的婚禮,在廣場上舉行時所發生的事,後來在村社裡流傳了許久。熱鬧的婚宴正要開始舉行時,牧師尤紐斯和頭目理加帶著一群人怒氣沖沖地出現,場面僵持不下,社裡有些人站在范勃亨這邊。這正是東印度公司所擔心會發生的情況,范勃亨在部落間的影響力,會在各地引起爭端。
學校老師Jan Druyvedaal和范勃亨一樣原本也是士兵,是新郎的好友。他帶著自己的妻子,大目降社的平埔族女孩來參加婚禮。他很有義氣地站在范勃亨的前面,擋住那些來鬧場的群眾。即使他這樣做也有可能使自己失去工作。
氣氛緊繃著,就連那些半赤裸的孩子都瞪著眼,手心緊捏著石頭,一場婚禮眼看就要演變成一場混亂的群架,遠處山區忽然傳來斷續的大砲聲,所有人都被這聲音吸引了注意力。
轟隆隆隆。轟隆。
…………………….
啪答。
啪答啪答。
啪答啪地咚咚咚嘩嘩嘩嘩--------------
大雨來的又急又快,熱帶的雨和家鄉不一樣。每一滴都像帶著重量,如同成熟的果實落下,揚起地上塵土的氣味。范勃亨抬起臉來,雨水和感動的淚水交融在一起。下雨了,終於下雨了。剛剛的大砲聲原來是山間先下雨所傳來的雷聲。
廣場上陷入狂喜,所有人都跳起舞來,包括那些尤紐斯牧師原本帶來鬧場的群眾。
下雨了,灑下的種子終於能冒出青翠的嫩芽,那些芽終於能長成豐收的稻稈。所有人因為這場雨,重新地充滿盼望。
神啊,我感謝你。
范勃亨在心裡喃喃自語。不知道是誰開始彈奏樂曲,婚宴在這個時候開始了。手上沒有樂器的,也撿拾地上掉落的樹夾敲打,彷彿這個時候如果不發出什麼歡快的聲響,心中的喜樂會從胸膛裡炸開來。
後來大家都說,從范勃亨和Tagutel 的婚禮開始,充沛而源源不絕的雨水,整整下了兩個禮拜。埤塘和溪流重新湧流起活水,植被又生意盎然起來。
雨水下了兩個禮拜,牧師尤紐斯也病了兩個禮拜。新港社的頭目理加帶著水果去探望他時,尤紐斯賭氣地一句話都不肯說。理加好不容易才忍住嘴邊的笑意,用他能夠做出最凝重的表情說:「咳,牧師,你知道,這一切真的是感謝神,你說是嗎?」
范勃亨已經不再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了,但新港社人視他為高大親切的紅毛親戚,因此不管是大員方面的地方政府,頭目理加,或是牧師尤紐斯,都無法從他們身邊把范勃亨趕走。
被解職的范勃亨還是一樣的忙碌,大員官方委託他協調附近山區村社的爭執。他每天早出晚歸,在各個部落間奔走。
Tagutel憂心兩個人未來的生計,問他,大員的人是否會給他薪水。范勃亨搖搖頭。
「既然這樣,為什麼還要為他們工作,這麼忙碌呢?」
Tagutel感到憤憤不平,但范勃亨安慰她:「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Tagutel在學校讀過,聖經上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汲汲營營為自己爭取權益的人,神會給予產業。Tagutel不再說話,心裡卻十分懷疑:這怎麼可能呢?因為范勃亨已經被下了禁止取得土地的命令。
大員官方的厚臉皮真是沒有盡頭。在山區村社的糾紛解決以後,隔年貢稅的收取出現問題,他們還是來找范勃亨幫忙。
村社代表不肯參加地方會議,也要找范勃亨出面邀請。
地方會議的翻譯阿勒豪夫生病了,范勃亨又被找去臨時代替。
凡此種種,台灣長官和議會,終於發現,他們實在是依賴范勃亨到幾乎不能沒有他的地步。而在接受了幾年范勃亨的無償服務之後,終於良心發現,在1648年的4月決議贈送范勃亨獎金150里爾為酬。
根據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的教授康培德,在「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這本書裡所記述的,在1654年,范勃亨被解職的8年之後,新任的台灣長官凱撒,視察大目降地區(新化)的田社,將現在在台南新市和新化之間一塊160甲的土地,給予范勃亨與他的同事Jan為財產。
這是范勃亨和Tagutel一起生活、養育兒女的土地。關於他們的後代,熱蘭遮城日誌的教會洗禮婚姻登記簿資料中,記載了范勃亨出生在新港社的女兒Susanna,後來嫁給了荷蘭Enkhuizen公司的員工Paulus Ossewaijer。
(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