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诗玲:在中国,八十年代被埋葬了但没有死
在中国,八十年代被埋葬了但没有死
蓝诗玲/文
王立秋/译
Julia Lovell, “The 1980s Are Buried but Not Dead in China”, FP, October 15,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10/15/the-1980s-are-buried-but-not-dead-in-china/。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意见,内容仅供参考。
蓝诗玲,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现代中国史与文学教授。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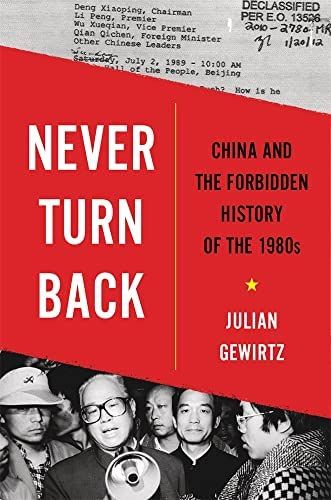
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永不回头:中国和八十年代的禁忌历史》(Never Turn Back: China and the Forbidden History of the 1980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32pp., $32.95(Hardcover), October 2022.
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访华的时候,八十年代在感觉上已经遥不可及了。在关于中国八十年代的英文书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公开、激烈地讨论生活的基本要素,包括毛时代(特别是其最具毁灭性的运动即文革)的遗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的现实意义、中共(CCP)在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
作为初次到访的游客,我亲身经历的中国截然不同:在这个地方,人们的精力全用在了追逐新的投机市场经济上,新闻自由似乎仅限于来回搬运首发于《人民日报》的领导人照片。到这个时候,“中国模式”看起来已经定型,那就是,由威权主义一党统治主持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国内的公共历史中,八十年代——那十年充满了开放的、富有想象力的可能性——留下的记忆及其确实性已经被彻底抹除了。
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出色的新书《永不回头:中国和八十年代的禁忌历史》(Never Turn Back: China and the Forbidden History of the 1980s)提供了迄今为止用英文写的,对八十年代活跃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之未来的激烈讨论的最详细的分析。自习2012年成为“最高领袖”以来,对历史写作、材料获取的控制大大强化。当然,中国的清零政策也使大多数西方研究者没法再亲自到中国待上个两年半左右的时间,目前我们也看不到重新放开的前景。
但顽强、足智多谋的格维茨已经通过对八十年代的长期关注,囤积了各种富有启发性的一手材料——泄露的内部文件、口述史、跳蚤市场的宣传指示——他也令人信服地使用了这些材料。
他的书从文革的结束和毛的离开写起。格维茨曾经是哈佛大学学者,现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他承认,就像冯客、马佳士等人已经展示的那样,七十年代初,农民已经开始划分自留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私人生产了。但在1976年毛去世的时候,贫穷和欠发达依然普遍存在。
巡回研究者发现农村惊人地贫困。在轻重工业和家庭消费上,中国落后西方和日本几年甚至几十年。在意识形态上,农村也濒临崩溃。在六十年代末文革开始的时候,对毛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点。到71年毛指定的接班人、和毛一起发动文革的林彪在据说暗杀毛未遂后出逃时坠机死亡的时候,激情开始消退。
毛去世后,党内的老人马上清洗其最亲近的盟友(包括他的妻子),结束文革。显然,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没了,可用什么来代替它呢?第一个选择是直接接替毛的华国锋在短暂执政期间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更难的选择是邓作出的。邓差不多和毛是同一辈人,他异常坚强地在文革的迫害中幸存下来,并于1978年罢免华,成为CCP的领袖。他解决毛留下的复杂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难题的方案是“现代化”。于是,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这个国家和党一直在讨论——有时是闭门讨论,有时直接在中国最大城市的街上和广场上畅谈——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在大多数情况下,邓坚持一个简单得乐观的定义。就像格维茨写的那样,他希望现代化就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变得更加“富裕”。他结束了毛时代对经济的狂热干预,给农民和企业家“更多决定种什么的自由,鼓励新形式的所有制来制造和销售服装、小玩意儿、家具等等”。他也愿意考虑政治改革,只要它能促进经济和市场改革。他愿意放权,加强商业法规以增强企业家的信心和活动,让旧意识形态的死硬派退休,为有能力的技术官员让路。
但邓温和的、以经济为重点的政改提议,也让其他人——包括那些深入政治体制的人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大胆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更为极端的批评。1980年秋,一名党内学者呼吁结束当对经济、文化和媒体的控制,并呼吁出版和司法独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全面政改的讨论在一度正统的会场逐渐常态化。《人民日报》的版面上也充斥着各种激进的提议:毛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一样残酷压迫个人;思想和言论应该“越来越开放和自由”。
CCP领导层的保守倾向和其他政治和思想精英无拘无束的思想之间的不适应造成了深刻的不稳定。八十年代中国最显著的合作与冲突,发生在邓和他的门人赵紫阳之间。赵是一位务实的总理,也是当时的党委书记,他主张中国应该对全球经济体系全面开放。
邓和其他高层的老人也乐于欢迎外国的投资和技术,有了这些投资和技术,这个国家才能赶上西方和日本。但在经济放松后悄然而至其他类型的西化(政治、社会、文化影响)深感不适。邓在1983年就说过,“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文字飞进来”。结果,整个八十年代,在高级领导人为“精神污染”(各种有害的外部影响,包括烫头、口红、走私和让-保罗·萨特)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与全球市场日益紧密结合的中国还起不起作用而争论不休的同时,中国也一直在自由化(“放”)和收紧(“收”)之间循环。
八十年代悲剧性的高潮——对全国范围的抗议的血腥镇压——经常被人们想象为一场二元对立的政治斗争,一方是支持民主的学生,另一方是决意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的官老爷。但格维茨也强调、至少是同样重视经济过热引发的争论。从88年中起,领导层就在争论通胀给政治稳定带来的风险。在多数时候得到邓支持的赵,即便在城市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也依然坚持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口号;1988年,中国的通胀率至少达到了百分之30。
到1989年的时候,中共政府面临一场由社会经济动荡和西式民主梦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个节骨眼上,经济的不稳定使赵显得不那么可靠。在当年春天“民主自由”的抗议呼声涌现的时候,赵的宽容立场——使中国对全球体系开放、对这样的自由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开放——受到了党内老人的责备,后者认为这样的立场就是在鼓励叛乱。格维茨提醒我们,对“动机不一(从要求民主到要求根除腐败和通胀)的抗议者”来说,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广场上一些最早的抗议者不是学生,而是担心物价上涨的工人。
用暴力来平息抗议的决定决定了中共领导人未来的方向,这与同年东欧做出的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强硬派在争论中获胜,派出PLA针对人民后,他们也改写了八十年代的历史,把它叙述为一个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只是因为赵未能保持“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纯洁”,才短暂地有所中断。他们重塑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把它改写为一条要求服从“一个‘核心’领袖”、服从CCP对马列毛思想定义的路,有效地取缔了公众关于中国政治的异见。
于是,八十年代的讨论(这些讨论经常是激烈的,但它们又是开放的,令人着迷)和毛本人一道,被正式地从历史上抹除了。CCP处理1989年的方式,也决定了此后领导层在大体上对西方的态度。在危机后,中国领导层是这样描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它们图谋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民主”。是境外势力的操纵导致了这场动乱。北京市长陈希同在1989年解释说:“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
在这十年间,人们为中国的未来而探索了各种各样的道路。格维茨的书为这些长期以来被国家主持的官方历史埋葬的道路提供了一种迷人的权威叙述。它使人想起后毛时代中国社会的活力,以及何以对八十年代末混乱的突发事件的回应,深刻地塑造了此后的中国。今天,中国的精英政治坚持,中国只有在一个威权的一党政府的统治下,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富裕的国家。格尔茨撰写的这部关于八十年代的重要历史提醒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争论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
附:原书目录
导论:禁忌的历史
1 重估历史,重塑现代化
第一部分:意识形态与宣传
2 精神污染和糖衣炮弹
3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祸根
第二部分:经济
4 解放生产力
5 市场的力量
第三部分:技术
6 回应新的技术革命
7 民族的生死问题
第四部分:政治现代化
8 国家的主人
9 无畏的探索
插图
第五部分:门之前
10 两轮掌声
11 大洪水
12 我们来的太晚了
第六部分:门及之后
13 政治镇压与叙事危机
14 重塑改革开放
15 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幸存者
结论:新时代
缩写
注释
致谢
索引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