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田野故事(9)井師傅的塔爾寺
一
井師傅的外公,曾經在四十年代末,用一根針換過一只羊。
那時候外公也就二十多歲,是一個掌握了漢語、藏語和蒙語的青海湟中塔爾寺人。許多年以後,他常對井師傅提起:“蒙語金,藏語銀,漢語銅,土語破麻衣”。意思是掌握了蒙語做生意最好,藏語和漢語次之,講土族的語言最不能賺錢。外公在很早的時候,就襲了自己父親的位置,為塔爾寺收租。當時,塔爾寺主要由位於湟中附近的六個藏族部落供養,它們每年會給寺院上交一定的糧食、牲口和金錢,來養活這裏的數千名僧人(1)。外公口才好,又懂得經營和變通,收租自然不是難事。平時,就輾轉於中國大陸做生意,把上海的物資轉運到西北的蒙區,藏區。有一年,外公去了青海南部牧區做生意,隨身帶著自己從上海買來的繡花針,當地人連針也沒見過,紛紛領著羊來換。此時,安徒生童話中老頭子用馬匹換了一堆爛蘋果的情節,已不再是傳說,而成了真實的故事。
講外公事跡的時候,井師傅淡藍色的眼睛顯得格外有神。這種瞳仁顏色來自母親的藏族血統。青海湟中人在人種學上來說非常復雜,因為這裏正好位於漢、藏、伊斯蘭等多元文化的十字路口,歷史上,各種不同樣貌特征的族群通婚和共融,形成了多樣性的人種特征。
井師傅的母親家是一個多民族大家庭,有藏族、蒙古族、土族、漢族等。外公年輕的時候,平時一家人坐在一起說話,通用語是藏語。然而隨著家裏人口的增多和老人的去世,通用語逐漸從藏語變成了漢語。常常是前面幾句問好的客氣話是藏語,而後面說正事的時候是漢語。“漢化也就是近二十幾年的事情”,井師傅說。
井師傅的父親是一個漢人,老婆也是漢人。我問他老婆:“妳們家從哪裏來?”她看一眼井師傅,挺直胸膛,驕傲地回答:“我們家譜上說從南京來!”
我問井師傅,“你父親的家從哪裏來?”。他堅定地說:“我們就是青海土生土長的漢族!”
他老婆於是對他投去鄙夷的目光:“你們家都沒家譜,還土生土長……”
井師傅這時急了:“怎麽沒有家譜?怎麽沒有家譜?我們家譜就是……可能丟了!”
我再問井師傅:“你的父親是漢族,母親是藏族,你怎麽當了藏族?”
井師傅提高了聲音:“我一直想改民族!現在能不能改民族?!我孩子大學出來了,改了也沒關系了,我不想當藏族了!” (2)
他老婆又投去了鄙夷的目光。我連問為什麽。
他說,在他外公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藏族人說話老是出爾反爾,還經常改變,不講誠信。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改民族!”他對著我,又一次憤憤地叫道,藍色的眼睛在燈光下分外犀利。
二
井師傅是個故事王。他是油漆工,經常在湟中挨家挨戶畫房子,對當地的神奇鬼怪如數家珍,尤其對塔爾寺故事十分精通。他講故事時,配合上篤定的表情、抑揚的語調和他淡藍色的眼睛,讓人覺得天方夜譚也如親身經歷,日常故事也神秘不堪。他的同事,為了聽他講塔爾寺的故事,在他家裏住了三天,最後還意猶未盡地走了。2011年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時,他給我講了半個晚上的鬼故事,當晚沒有月光,我聽完故事一個人睡在他家新蓋的八十平,只有一張床的客廳裏,對著玻璃外黑乎乎的花園,直到淩晨四點才敢合眼。
1969年,5歲的井師傅第一次被叔叔領到塔爾寺去玩。那時候他並不知道塔爾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誕生地和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望著這空寂而龐大的建築群,他好像發現了家附近一個新的遊樂場。從此以後,這個小男孩便每天跑到寺裏玩,這也使他成了當時看管寺院的為數不多的老阿卡的好朋友。1958年,青海開始了宗教改革,塔爾寺中的絕大多數僧人被遣回原籍,強制還俗,還有數人被囚禁,勞教、判刑。在這裏成立了塔爾寺管理委員會以及由部分僧侶組成的生產隊,而看守寺院的任務就落在了十余個老阿卡身上。年幼的井師傅就在塔爾寺一個個院落裏竄來竄去,而孤獨的老阿卡們也十分歡迎他。他們常常牽著他的手,給他看每一座佛像,每一個佛塔,給他講每一張壁畫背後的含義,以及流傳在塔爾寺數百年的傳奇故事。

井師傅於是親手摸過塔爾寺中手掌般大小的夜明珠,四個黃金制做的宮燈,看過塔爾寺至今秘而不宣的歡喜佛,爬過傳說中埋藏宗喀巴胞衣處的菩提樹。他每天樂呵呵地上去,摘幾片樹葉,拿到外面送給穿著皮袍偷偷朝聖的藏族人。他也曾靜靜地待在老阿卡旁邊曬太陽,看他們偷偷地念經,看過太陽升起後阿卡生產隊向毛主席像請示後的出工。每天,他在太陽出山時去寺院,天黑下來才回家,就這樣度過了他的童年時代。塔爾寺的壁畫故事和神奇傳說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對他來說,這比湟中一個月每天連續放映的樣板戲有趣多了。
1979年,塔爾寺再次對外開放。官方統計報告中顯示,1957年這裏有1615名僧人,而開放的那一年,只有64人。(3)
少年的井師傅站在寺院外,看著塔爾寺二十余年中還俗娶妻的僧人們繞著寺院一圈又一圈地磕長頭懺悔;看著龐大的寺院因為重建一點又一點地被拆遷,一座座幾百年的壁畫墻轟然倒塌;看著原來被幹部們占領的活佛和阿卡家被歸還寺院,以及改造僧人住宅過程中,塔爾寺一點點變小,變小——變得連歡喜佛都被遮蓋,連鎏金大佛腳下的故事也看不見。
井師傅最後一次去塔爾寺是20世紀80年代末,這也成了他與塔爾寺的最後一次會面。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去過,甚至沒有接近過那裏。因為這一年,他在塔爾寺的最後一個老朋友,不在了。
註釋:
(1)《青海塔爾寺歷史大事編年》中提到,1944年12月青海省戶口調查,直屬塔爾寺682戶,2272人。而1957年出版的青海省文史館著的《塔爾寺》一書中提到(第18頁),民國時代塔爾寺僧人數量曾一度達到三千六百名,因受地方政府盤剝,臨1949年時減少為一千一百名。
(2)在青海,擁有少數民族的身份可以在升學考試,生育,法定假期等方面享受優惠政策。所以在當地的漢人和其他民族組成的家庭中,孩子出生後申報身份信息時,多選擇非漢族身份。
(3)“當時(1958年),塔爾寺有僧人1615人,其中內蒙古籍530人,有內蒙古方面派車接走,(回蒙古後部分人被捕),青海籍一千多人(其中土族約500人,蒙古族,藏族約500人)被集訓。當時劃為宗教上層的280人,捕辦的約300人,在廢除寺院封建宗教制度的同時,出現了防判鬥爭擴大化的問題,從8月10日起,又陸續捕辦、集訓近二百人,當時共捕辦活佛,僧人427人,還有部分人集訓後,往農村監督改造。” 《青海塔爾寺歷史大事編年》,《湟中文史資料第四輯》魏明章編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湟中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內部資料)湟中縣印刷廠印制,第62頁。“僧人除看守寺院殿堂文物外,參加勞動,按工分配口糧。留寺的120名中,以後又有回鄉和去世的,到1979年只剩下64人,組成一個生產隊,耕地500畝。” 出處同上,第65到66頁。
更多這一系列的故事,請關注標籤 Fishear的人類學田野故事
標籤內容不定期更新,取決於作者的體力,心情和懶度,謝謝您的耐心,陪伴和關注!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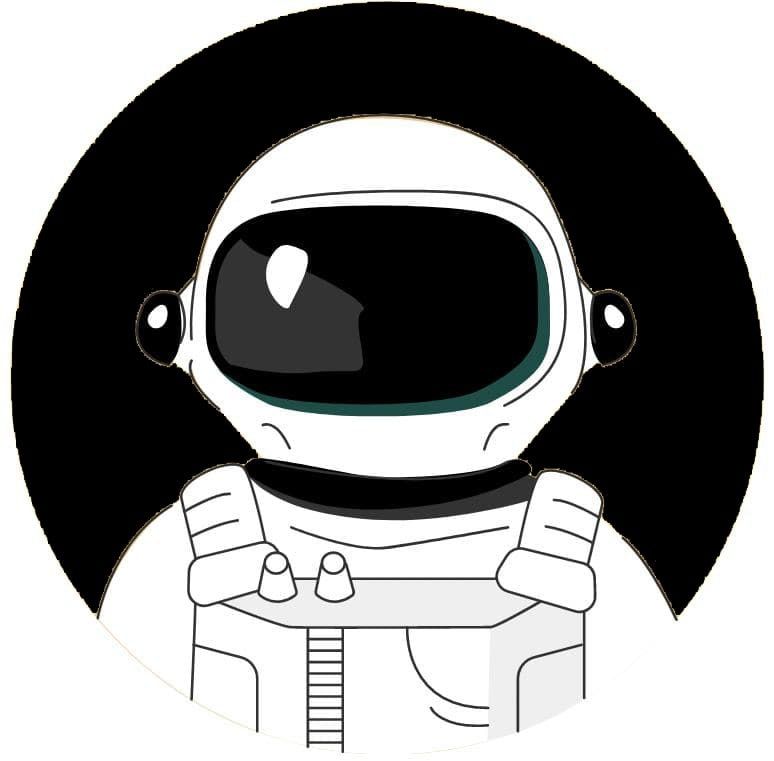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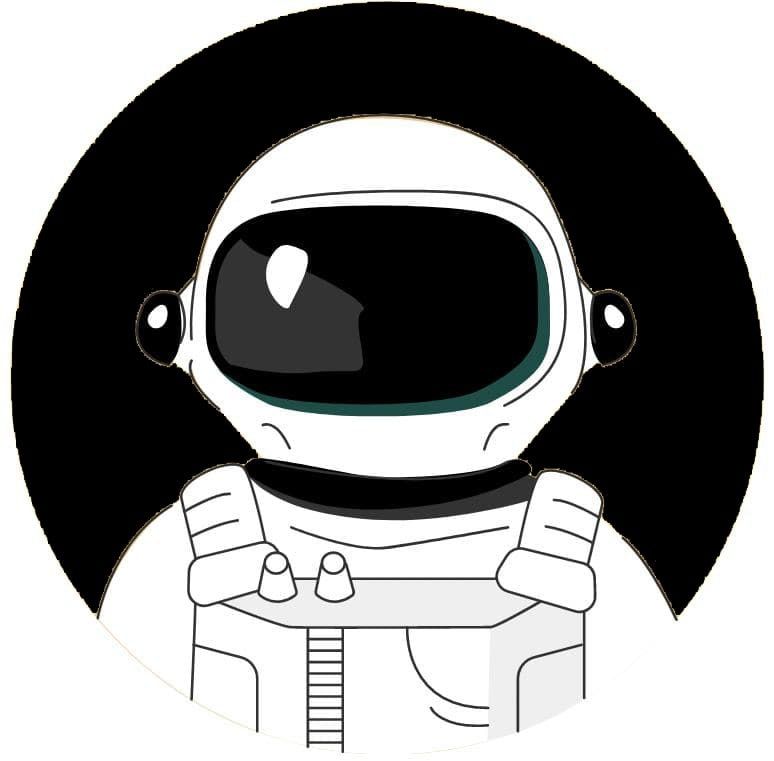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