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他們的眼睛,我一點也不害怕
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為硝煙彌漫戰場的後一天,我看到克里斯托在FB說有沒有人要一起去中文大學或沙田法院。
我想去!我跟克里斯托和霜霜說,但全城交通癱瘓,中文大學那邊道路更是無法過去。
終於下午地鐵站有所恢復,我們決定去自己的學校看看,中大「戰役」後,浸大也許要開始。
我和霜霜說,可以去學校找住校讀Mphil的好友Kyle一起玩,圖書館食堂都不開,但可以去他宿舍。
在九龍塘地鐵站,我們等到克里斯托。從A2口出站不久,就遠遠看到,一群黑衣人在設置路障。霜霜還有那晚催淚彈後遺症,不敢過去,想從另一條路走。
我和克里斯托心裡都很想看人,我勸霜霜說,沒事的,不用怕,我們就一起從這過去。
我無法感同身受她的懼意。不过想那就跟她從後面繞路走吧,但她又很理解我心裡的渴望,讓我跟克里斯托一起去看,她自己從後面去坐巴士。
我跟克里斯托站在那兒看了一會兒,那些都是和我們差不多大甚至比我們小的年輕人,在一邊努力的設置路障,一邊指導車子路過。
看到兩個感動的畫面。有個媽媽牽著小姑娘路過,黑衣少年協助他們。
再過幾分鐘,我正看著著從馬路過來的一個戴眼鏡的黑衣男孩,感覺上一秒他也在看著我,下一秒,他就過來幫忙推身邊老人的輪椅過階梯。
都是一瞬間的事情,想拿出手機來拍都已發生完畢。
好遺憾,沒有捕捉到這些感動的瞬間啊。
語言畢竟沒有視頻有實證力量。

我在路上跟霜霜發微信說,剛剛發生了兩件感動的事。
她說「我覺得我會後悔,我把這樣的場面想的太可怕,雖然知道他們的目的又不是傷害我們,但是還是怕,那你這樣, 我好感動。」

我和克里斯托沿著聯合道一路走,路上的磚頭陣像藝術品。有姑娘在墻上噴字:香港人,報仇。
有兩個男生在跟一個老師坐在那兒聊天,有人推著裝磚頭的車,有人在地上撬磚,我和克里斯托都非穿黑衣,我用手機拍她用拍立得,沒人過來管我們。

後來我把拍的一張撬磚場景的圖發在Ins上,有兩個在媒體工作的同學私信問我,是如何得到他們的拍照許可的,他們沒說不給拍之類的嗎。同學說,見到新聞被私了的說都是因為拍照。

我說,可能下午學校這些都是學生吧,所以還好。
走進熟悉的校園,有一些外國面孔,有人坐在地上吃飯,圖書館外面各種水、糧油和零食。

九成的人都穿著黑色衣服。我給霜霜發微信說「看著他們的眼睛,我一點也不害怕。」
走進傳理大樓,沒有什麼人,和霜霜在8樓會合,一起去Kyle的宿舍。
就在我們在宿舍聊天的時候,香港各大高校陸續宣佈這學期停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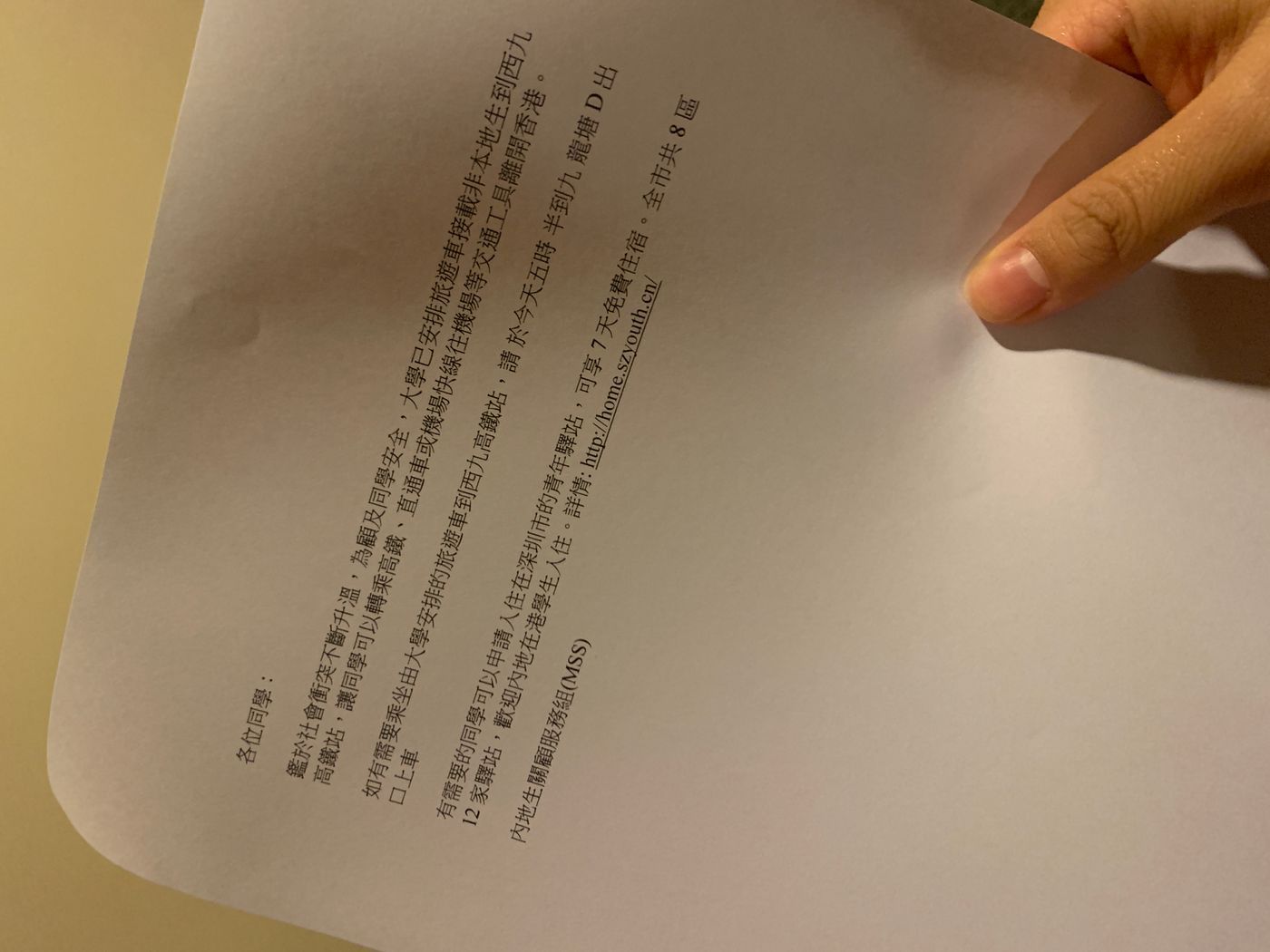
下午五點多,我們從宿舍出來時,撿到塞進門里的一張紙,是內地生顧問服務組說由於局勢升溫,安排內地生坐大巴到西九龍高鐵站返回大陸。
在宿舍樓下,真的看到兩個拿著行李箱的內地同學,一男一女,女孩今年剛來香港讀環境科學研究生。
我們一起往地鐵站走去,在傳理學院旁邊一條路上,黑衣人已經用鐵欄杆等將路封起,需要翻過去才行,拖行李箱的兩個同學站在那兒,不敢前進。
Kyle用粵語跟黑衣人說,我們是不是就從這過去,黑衣人點頭。然後我們就一個個跨過去。

霜霜不再是最怕的那個人,還幫那兩個同學過來。
後面我們跟那個女生聊天,問她你剛剛不是很怕,她說「刚刚在那看到他们那群人,都要吓哭了,好怕他们一磚頭就扔过来。」
女孩說,可能因為自己住學校,第一次出来看到这样的场景,之前都是在電視上看。她沒有香港朋友,也不會講「他們的語言」。
「你会怕警察吗?」我好奇问道。
「警察我不怕呀。」

我想到我第一次有点害怕是蒙面法那晚,在太子站跟一群街坊在一起時,看到旺角警署探出的頭盔和身後突然出現的防暴,想到老郝有次穿黑西裝走在去北角聽講座路上,一個阿婆拉住她小聲說「今晚有狗」。
而昨天,红磡的保安大爷嚴肅說,你們趕緊回大陸,要注意,兩邊都有危險。而我老覺得自己的身份,其實兩邊都不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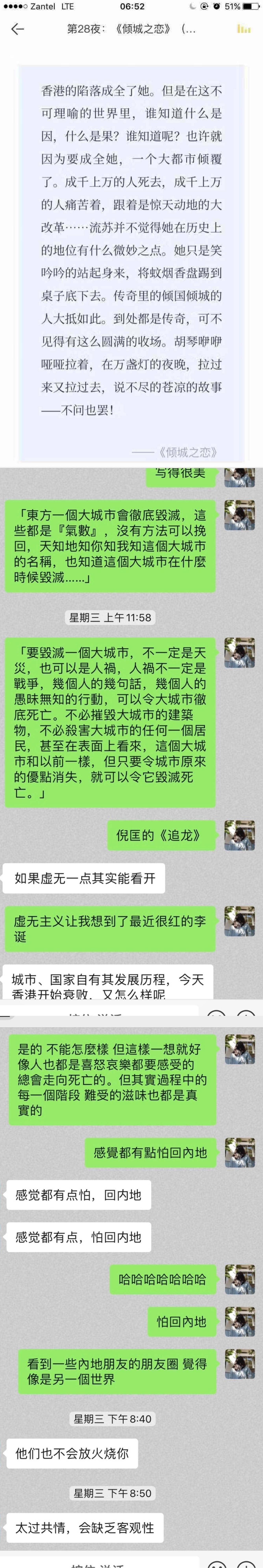
總之,那天,很多內地生離開香港。那晚,我們以為浸大會發生什麼。
並沒發生什麼。
晚上8點,接到美国姑娘Rachel的ins通话,Rachel有个在前线做急救工作的男友,几乎每场示威活动她都会去。看到我下午发的黑衣人和砖头照片,她问我在哪。
她說她現在在學校,后面是protesters,但沒有警察,一切都很平靜,peaceful。看來中文大學的激烈對峙沒有再複製。
就在港中文成为硝烟弥漫战场的前兩天,我和幾個朋友在中大旁听秦晖老师的历史课。
那個週六,秦暉老師講黃宗羲,講“反法之儒如何學西”,講黃對學校的設想,我瞟見自己當天筆記裡這樣一句話:學校顯然不能只是教育機構,學校不止自治,還有治天下之職。
當時粗粗記下這句話,沒什麼過深思考,只是覺得,香港的學校明明是個總讓我覺得快活又充實的地方。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