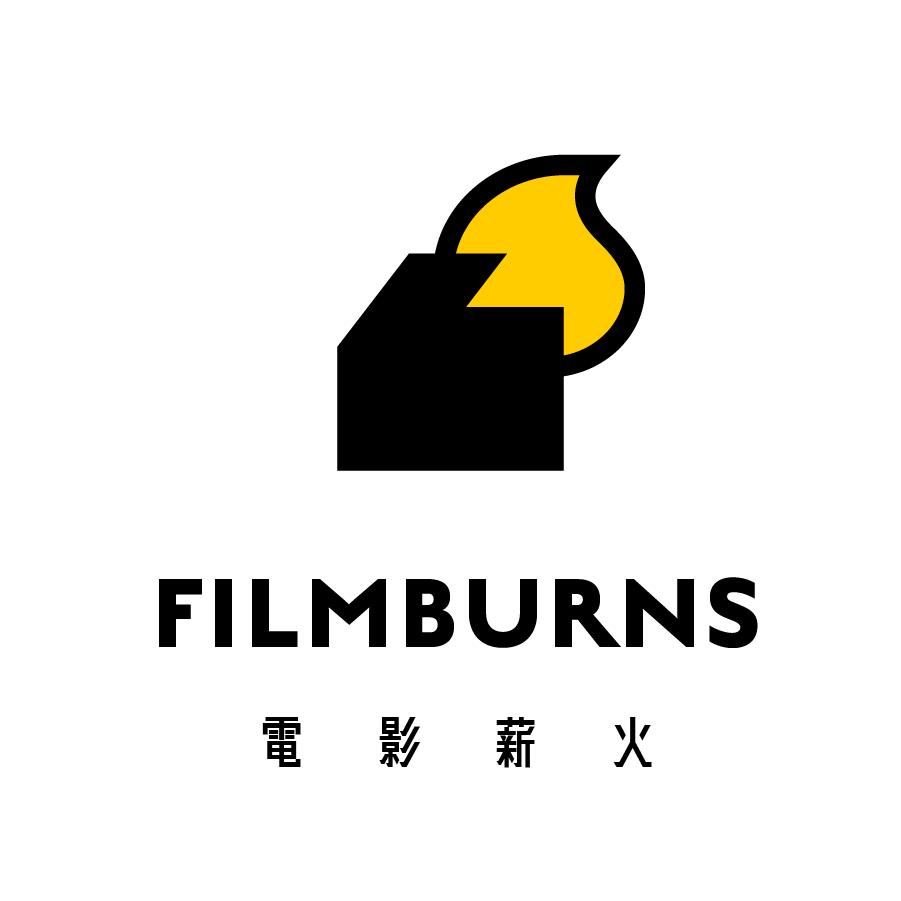《怪物》:成年人聽不到的樂章

文|中田
是枝裕和的新作《怪物》,在某個意義上,似 2017 年佈局奇詭的《第三度殺人》,重點經營層層遞進的懸疑戲劇,有別於他常拍的親情題材。這次是枝裕和找來兩位具份量、標誌性的創作人——資深的日劇編劇家坂元裕二、我們尊敬的「教授」坂本龍一配樂——聯手創造《怪物》剖析日本與小孩情感的世界。三位在其領域(電影、編劇、音樂)都可稱為作者的創作人,在《怪物》的藝術風格展現較從前內斂,整齣電影像是三人的協奏曲,互相成全,共奏一首成年人聽不懂、聽不到的樂章。
(《怪物》是一齣需要保護劇情謎底的作品,建議看完電影才閱讀下文)

《怪物》開場以孩子星川依里在湖岸草坪的步履及大廈火警掀起序幕(片名「怪物」二字浮印在受大火焚毁的大廈),坂本龍一的琴弦伴隨煞有介事的視點鋪排(先以視角有限的母親察覺到兒子麥野湊不尋常的行徑),氣氛神秘又嚴肅,有如日籍韓裔導演李相日的多視點作品、同樣是教授編寫配樂的《怒》。電影精心鋪排起一個疑團,引導觀眾預期這是一部關於欺凌事件的驚慄 / 社會議題片。然而當各人的敘事角度慢慢擴展事件的全貌,《怪物》的藝術造詣便不止於其多角度交織的劇本結構,或是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因為故事根本不複雜,沒有難以啟齒的「真相」——高明的是編劇利用戲劇結構引發的懸念,教觀眾注視每樣微小事情,隱現背後的情感與社會的固有問題。

從結構鋪排(次序是母親、老師、校長、孩子的視角)及故事所佔篇幅而論,電影有意在成年人和小孩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高牆,前者永遠無法進入後者童稚的世界。《怪物》首先由大人世故的眼睛看待事件:身為人母要讓欺凌兒子的壞人道歉和受到懲罰、校長和老師們為了學校聲譽而草草認罪道歉、母親與老師觀察到孩子的異樣(麥野的言行反常,星川有讀寫障礙及身體傷痕),在危急關頭(兇猛的暴風雨來襲)才發現事情尚未平息;後來才從小孩(麥野和星川)的角度回頭經歷,反過來顛覆成人的想像,孩子沒有突然遭逢甚麼壞事——受同學和父親欺凌已經習以為常——而是因為兩個男孩對彼此產生超越友誼的情愫,心神錯亂,促使所有一反常態的行為,導致成年人的誤解。
因此角色幾次提及的「怪物」只是幌子,故事裡沒有戲劇意義上的反派(克制的敘事角度只暗場交代星川父親對兒子造成的傷害),劇本真正聚焦的是兩個男生的純真和情誼。星川在雜物房請麥野吃點心麵,是他們美麗友誼的開始(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這段友情之所以神秘、不可告人,除了是麥野害怕被聯群欺凌的緣故,還隱含了剛萌芽的同性情誼。坂本裕二敘事鋪排具策略性,他首先讓我們從成人的眼睛,確實地看清事情本身反映的社會真相——在日本社會盛行的謠言風氣、群體利益 / 團結對個人有壓倒性的力量——將事情逐一以理性的角度觀察後,才把我們投入孩子率真簡單的世界,跟他們一起穿過隧道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說著宇宙大擠壓的奇思幻想。在建立扎實的社會背景和文化風俗後,麥野在重要關頭壓抑對星川的感覺、星川自認 / 被父親認定是怪物,情節上就更具力量,令人明白孩子表達感情的阻礙。

《怪物》對日本追求群體團結的社會風氣固然有反對的意味(受謠言中傷的老師便是其中的受害人),不過電影無意對此強加批判,編劇坂元裕二的敘事取態志在呈現小孩向大人表達自己的困難,麥野無法向無微不至的母親坦白心事、星川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老師未能讓學生打開心扉。臨近末段,校長嘗試開導因同性感情而困惑的麥野,也不是教誨他把事情說出來,而是讓他把不能說的話,用管樂吹奏出來,意味著他們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壓抑,不一定要公諸於世或表達真正的自我,卻需要明白任何人也可擁有幸福。
所以《怪物》在骨子裡可說是保守的電影,故事低調地使觀眾反應,溫柔地讓人看見日本小城市社會的面貌。它以平實的劇情發展,叫人意識到日本孩子的同志情誼面對的壓抑,及社會對個人的凌壓。作品終於獲得康城影展的最佳劇本獎及酷兒棕櫚獎,頗能代表本片的藝術成就。編劇坂元裕二用敘事結構抓住觀眾和營造戲劇性;導演是枝裕和憑演員指導和簡約的場面調度提鍊自然;配樂坂本龍一繼續以音樂彰顯人類內心深處的掙扎和解放,最後是枝裕和將兩小無猜的純真寄放在〈Aqua〉,為坂本龍一的電影生涯畫上了一個純白的休止符。
天堂一切安好。聽完〈Aqua〉的我,有這樣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