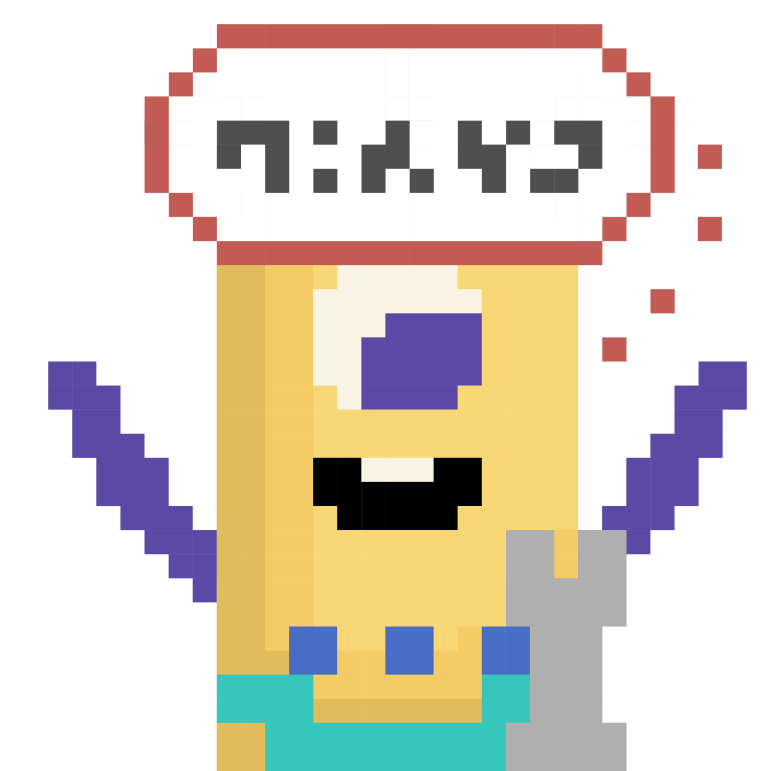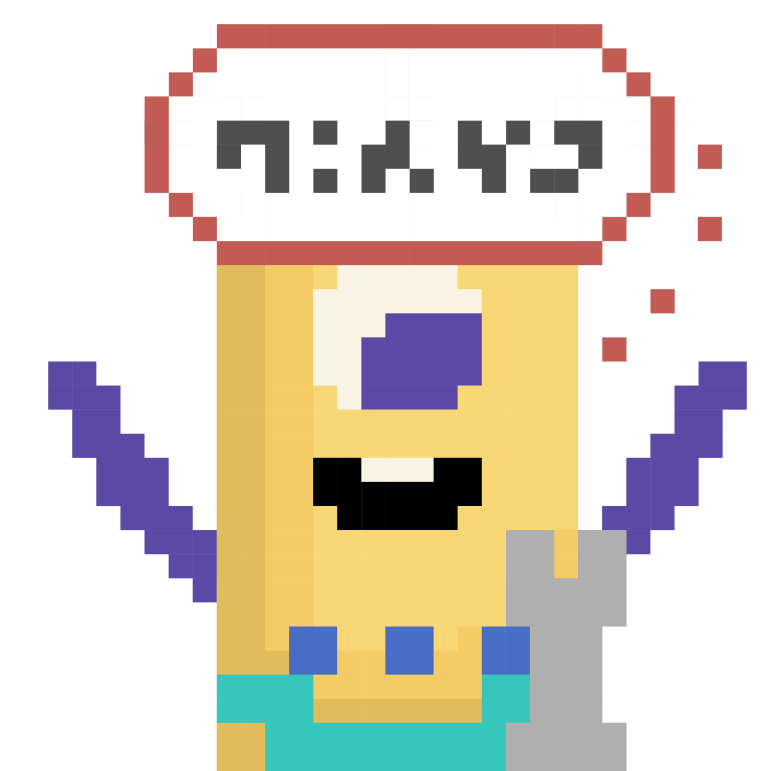世界坠落的速度总是快过一切
中国的“女权主义”在众多的女权活动家遭到抑制和抓捕时,也没有掀起多少声浪,她们留下的声音微乎其微。但是在北大三女采访上野千鹤子时却被突然点燃,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讨论"女权",尤其是那些从未关心过女性困境的投机者,争先恐后。
老实说我已经受够了,持续将这三个女人架在火上烤有什么意思,最后只能得到男权社会的一声嗤笑:怎么样,你们这个女权主义"不正宗"吧,连你们自己都这么认为。
男性知识分子拐弯抹角地批评三个北大女生没有教养,学识配不上北大这个名校。他们想要撕碎的岂止这三人,而是包括任何敢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的中国女人,他们只能给出“三个好女权”名额,往后讨论的空间也将进一步紧缩,男权总会得到他们想要的发言人,或用尽手段将其收编。
但作为这场"风波"的当事人,上野千鹤子在后来与戴锦华的对谈中却提到:"我接受了来自中国媒体的犀利采访,我觉得中国采访者比日本采访者更能切中要害。"我愿意相信这并不是出于恭维的目的,她真的用心倾听了这些问题。而彼时得知我的女同学也正在遭受婚姻和生育的胁迫及自困,我更加确信那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女权活动家叶海燕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写道:"她们的提问很真实,非常有代表性。她们只是借与上野的对话来引入中国女性群体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关于女性的问题,没有什么等级之分。没有什么问题是高大上,或者什么是低小下。只要是涉及女性的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
这对我很有启发,我原先也是愤怒的一员,在看到整个活动背后的操作后更加感到愤怒,甚至是悲伤。我为什么不愿意谈论此事,它让我感觉是在这个本就不剩下什么"女权"的地方,最后实施的某种卑劣的清场,所有人的声音都会化作它倒下的那一声震响。
但是在今天,我仍然回顾它,希望它不会如我所想的那样轻易落幕,而是无限绵延下去:我们想补充什么,我们想看什么,我们还想问什么——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而不是像有些媒体故作姿态地贴出标题:“上野千鹤子,不要回答。”我们已经受够了长久以来的沉默和失语,我们应当继续说下去,哪怕是错的,也仍有转圜的余地。
今天是 2023 年 3 月 8 日,我总是在这之前的一段日子里,如此频繁而具体地想起去年、前年与此相近的时光,好像因为这个日子,女性总是容易回到起点。这个起点不知是好是坏,如果是现实的、历史的起点,是否也就意味着始终没走出这个圈,如果是一个必须回望的出发点,也许可以为我们导正方向,给予更多的勇气。无论如何,这一天是重要的,它提醒我们过往的时间、以及尚未到来的时间都同等重要,也同样值得争取。
但今年也没有什么"好消息",世界坠落的速度总是快过一切。更糟糕的是去年就在关注的"铁链女"事件至今也没有后续,在防疫的尾声中前往丰县的人统统被拦截在外,旧的罪恶仿佛铜墙铁壁,不可撼动分毫。为其发声而遭到抓捕的乌衣杳无音讯;因反对封控参与抗议而被清算的众多女子仍没有释放的消息;香港的"三·八"妇女节游行最终被取消;企业辞退遭受性侵的女员工,原因是其"有风险,会影响公司形象";受尽男权凌辱的女主播因被剥夺谋生机会而决意自杀,却换来互联网上如潮的荡妇羞辱;一个女子被当众强暴,警方通报里却无耻地写道:二人是夫妻,衣服为她自己所脱……
而世上其他地方呢,伊朗女性持续抗议且不断遭受打压,塔利班宣布禁止阿富汗女性接受教育已超过五百多天,最新消息是女性即使在遭受家暴的情况下也将被禁止与其丈夫离婚,所有向女性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均被勒令关闭。日本政府相关人员茂木敏充在推特展示了全员男性议员的合影照片,日本女权活动家转发称“没有女性的国家,日本”,随后日本财团于"国际妇女节"前夕发布了"世界女性议员比例"统计,该数据显示,从1946年至2021年,女性议员的比例仅增长了1.3%,网民评论:日本的时间停止了。
正如海蒂·哈特曼在 70 年代就已发出的感慨:“我们的运动已经不再处于那个令人兴奋的,精力充沛的时期,那时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有用:提高意识,把更多的女性(甚至比能容纳的更多)带入运动,在社会中增加女性问题的可见性,通常以一种在根本上挑战资本主义和父权关系的方式进行。”如今我们恐怕更是不知道自己身在历史何处。但也许“起点”存在的作用就是这个,它时刻提醒我们可以重新进行评估和分析,以瞄准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
你不得不承认,"女权主义者"在我们的世界就已经并不是什么令人尊敬的称谓,不是一枚闪光的勋章,没有人因为戴上它而获得荣耀。大多数时候,世界会用一种轻佻的眼光注视你,寻找不解的根源,然后安心地背过身去,不再信任你说的任何话,因为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当你返回到文学的领域、一切你热爱的领域,那里有一个固若金汤的秩序,只要你显现出一点不满,都会被视为将其当作武器,心怀不轨地刺探那庄严神圣的殿堂。哪怕被迫要承认你,他们也会先将你从那个位置开除,确保那里再也没有你的一席之地——"女权主义"就是这样被吸收,用来反对女性的。
按照书上说的和人们的反应,我更是不知不觉成长为“激进女权主义者”。这种迟来的自觉和无时无刻的愤怒,首先让我感觉到莫名的悲伤和苦涩,好像起初无意走到这里,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人烟开始稀少起来,意味着理解你的人将越来越少,你受到的攻击将越来越多,而最为重要的是,“激进”是否意味着真的有危害,是发现新大陆还是走入死胡同,有黑暗的一面最终将自己吞噬。
可是假设按照海蒂·哈特曼的说法——“激进女性主义的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口号。她们认为,女性的不满并不是出于适应不良者的神经质的衰叹,而是对这个女性被系统地支配、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结构的反应。”那又有什么激进的?担心个人被政治吞噬吗?个体的特征在庞大的集体运动中被抹除吗?我无法给出意见,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对“女权”和“运动”的补充,而并非就可以用来作为“反女权”的根据,最好能达成中间的共识——让所有人更好地生活下去。这也是我理解的“政治”的含义,所以有时候我并不反感它。
我在去年使用了“社会主义的女儿”一词,却未能探究其中蕴含的这桩“必然的悲剧”: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迄今为止的任何形式上都是不平等的。提出这一观点的正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海蒂·哈特曼,她在 70 年代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不快乐的婚姻:导向更进步的结合》,反省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解放问题。她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女性主义分析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女性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都是必要的,但事实上女性主义一直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因为它们将女性主义斗争纳入了反对资本的「更大的」斗争中。
这大概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女儿们”天然感到痛苦的重要原因,作为纲领的那个主义是不会轻易让步的,需要你的时候,女权运动就是“社会主义事业”,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寻衅滋事”、“挑动性别对立”、“破坏社会安定”。
马克思主义和它所反抗的资本主义一样,是性别盲目的。在大量争取工人权益、优先考虑“阶级”的议题和运动中,参与的女性都会惊骇地发现她的“同盟者”并没有将她当作“同盟”,而仅仅看作是女人——不少男性被曝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的恶劣行为。我想他们喊出的关于“解放无产阶级”的口号也许并不假,而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女权主义”往最好了说也不如“阶级冲突”重要。」
或者今天他们已不再说“阶级冲突”,而是“没有人权还谈什么女权”,这种新的从属关系强行将二者对立,非要人从中二选其一,不允许女性再强调女权、认为关注女权会削弱人权的重要地位,而是必须加入到他们广大的同盟中去,因为解放了所有人,女人自然也会得到解放——这种论调不熟悉吗?既然我们能理解现实困境并非由单个议题构成的,又怎么能够期望解决了它就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聪明的女权主义者,我就会说,在女性解放运动中,真正的敌人是所有人共同的压迫者——历史意志。但必须追问的是,庞大的历史意志究竟寄身于什么之上,我们不可能对抗一个无法被指认的东西。或者退一步踏入虚无,承认所有的"主义"和"运动"都是无效的,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历史的发展取决于无数的巧合与阴差阳错。但我还是想做这种笨蛋,我还是想持续地做点什么——如果什么都不做,电视节目里将永远播的是减肥、美容和性爱秘诀,像我小时候所经历的那样。所有的产品都和家务劳动有关,好像女性面临的生活处境就只有这个,而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告诉我们应掌握的唯一知识。
2023 年的妇女节,哪怕我们学会从内衣和化妆品广告中解脱出来,“尝试阅读政府工作报告为消遣”,但是在这一天中也尚未感觉到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也没有更伟大的祝愿,而仅仅先从快乐开始,先和自己的身份和解——哪怕是出于"私愤"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哪怕真正想获得的并不是清白的真理,而是世上的权力……别人已经那样苛求你,你不妨多给自己一些宽容,承认自己的欲望并为其负责,道德不可能是个人的东西,也不可能是女性的东西。
在这一天,祝我们能够保全自由——同时保持可抵制性、开放性、创造性和不完整性,这是女权主义的活力之所在。
世界坠落的速度总是快过一切,但我们有无法被扑灭的火——“有一种能够发火之物能够自燃,无需人点——当漫长的黑夜刚过——你无法把洪水包裹起来——放在一个抽屉里边——因为风会把它找到——再告诉你的松木地板。”
2023 年 3 月 8 日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