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段拉拉之爱:肉体、欺骗与渴望

别的女孩:对于爱情,我们早已说倦。就让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实开诚布公:爱是量产于丰盛年代的稀缺金属,“比金子更少,比昙花更短暂,比铁树开花更艰难。” 事已至此,不如躺平。
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个二十多岁才刚刚开始探索恋爱、此前从未与人建立过任何亲密关系的女孩。她的所有关于爱的想象来自文学,一切关于爱的练习发生在交友软件。这很当代,但随后发生的事十分古老:像一只初次踏入黑暗森林的小兽,她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爱欲的饥渴,爱而不得、身不由己。显然,这无关性别。但凡在漩涡里挣扎过的你,必定会懂。
欢迎打开我们的全新专栏 #不爱也行#。这里拒绝任何关于爱的陈词滥调,取而代之的是后爱欲时代的虚无与清醒。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女孩,欢迎说出你的故事:biedegirls@yishiyis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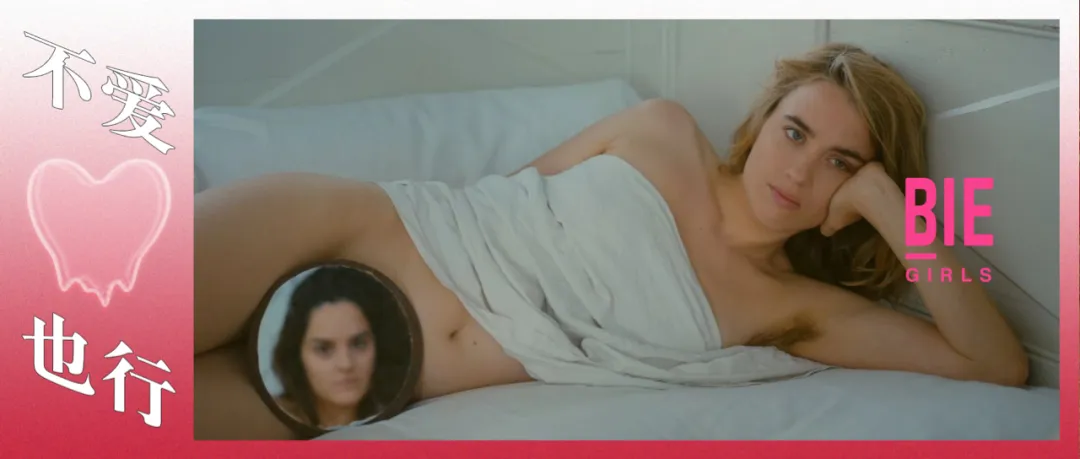
仲 侣
▼
1.
“爱的初体验”
从初高中到大学,我一直信仰着爱情小说里的 “恋爱靠运气”。好友小丁却说恋爱是要谋取的,需要计划一步一步猎得。那时,小丁正对新生群的同校同学穷追不舍,作出了缜密的恋爱作战计划。我缺了一大截课,茫然中掉队几千公里,要在一个新的领域重头学起。
研究生毕业后,身边同学开始有余暇关注情感生活。至于我,原有被学业占据的生活空出一大块后,突然觉察出情感的空虚 —— 还夹杂着一种从未为恋爱努力过的不安。那种感觉就好比高考时做数学卷,在前面的选择题应用题花去大半时间,翻到最后一面才发觉有一条占分80分的大题。
直到我遇见 A。她是我在 Tinder 上划到的香港女生,聪明、好看、思维活跃。与她交往,是我第一次察觉到爱欲的形状。从认识 A 的第一天起,我的情绪就全天候持续高涨起伏,常常在数分钟之内从甜蜜变为暴怒 ——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感到 A 并不考虑我的心情。
过去的我活得很简单。我感到自己是无性别的,像悬浮在世界半空的透明小人儿,一切情感都能在我身上投影,亦能毫无障碍地穿过我。而此刻的爱欲来得汹涌,犹如陷入高烧,无法阅读,无法表达,社交媒体的零碎信息也接收失败。
意识到我的失控,A 很快疏远了我。
峰值过后,我的情感从高位渐渐跌落到低位。我百无聊赖地约会着新人,维持着心有所牵的状态。我的第一段爱之体验,就这样结束掉了。
2.
“这个人我也并不讨厌”
2019年,我从香港毕业来到深圳,在 Tinder 上划到了钟汶。她第一张相片是猫,第二张是咖啡、相机,第三张才是她的样子。戴着眼镜,是我喜欢的类型,但只得半边脸。
Tinder 交友,与现实生活中遵循着不一样的逻辑。在这里,个人的特质被放在数据里量化,最受关注的是两样东西:相貌和有趣。这两样初步 Match 以后,开始查户口式聊天,以坐标、是否单身、喜欢的事情来判断对方是否在择友范围内,择的又是怎样的友;或是针对对方的资料给出些故作有趣的反应,来测试双方是否同频。
钟汶询问我一番在拉拉关系里的属性、长短发等信息以后,我们约了见面。当天她没戴眼镜,样子秀气,身形略壮,但和照片有差。我放下紧张的心,像朋友一般交谈。晚饭后,我以为会各自告别 —— 毕竟我自觉不在约会状态里 —— 但她提出一起散步。
我们从中环散步到赛马会跑马场,发现我们在香港同一个学校毕业,认识同一位有名同学。我们在跑马场游乐场的转椅坐下。她拿出一包烟草和一个卷烟器,往烟纸里放了烟草、滤嘴,径直卷起烟来。
她舔了一下烟纸边缘,把烟纸黏合、卷好,问我要吗。
我说好。
我们走到游乐场旁的马路边上,靠着垃圾桶抽烟,没两口我呛着,钟汶接过剩下那半根烟。望着红绿灯,我突然感受到月亮走得很慢。
晚上我回到深圳,以为相隔两地的陌生网友再无后话,结果第二天钟汶又找我聊天。正当我想着 “这次好像可以”,钟汶问:其实你为什么玩这个 APP。
我心想来了,每一次关系都会有不对劲的地方,我又到这里了。
我过往对情感的认知 —— 更准确地说,是我意识到 “恋爱” 这个领域的存在后,我仅有的情感练习,全部发生在约会软件上。这些练习无一例外,指向同一套模式:先是兴趣范围内的聊天,大概一到两天后会有涉及 SEX 的聊天,一周后见面,继而发展至上床。
我老实回复道:“找女朋友。” 她说她不是。
我心想,没有爱的话,有杏也可以。这个人我也并不讨厌。
3.
“身体像某种开关把我们打开”
见面第二晚,钟汶说出她并不想进入严肃关系。我突然松了一口气。
那我们就是P友,我在心里想。
既然是P友,我就可以更自如地应对。第二次见面,我和钟汶上了床。此前我没有过经验,仅在见面之前在微博上饱览了拉拉博主写的杏知识。希望不要露馅。
钟汶进入房间后打开电视,我们坐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影,她开始一点点地触碰我,蝴蝶在我身上停下又飞走,鳞粉掉落在皮肤上,留下斑点荧光。我靠在她的手臂里,她穿着毛衣,我们都出了薄薄一层汗。
电视上还播着黑白的文艺片,主角的交谈声变得只剩耳边一点悠长的蜂鸣,近在咫尺的喘气声被无限放大。我们在密集的吻之间大口呼吸,在沼泽里持续下陷。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身体的存在,它的灵动和敏感令我感叹。此时,我感到原本的我抽离在上空,似乎在她亲过来的刹那,另一个我走进了混沌的时空,在无数纷乱的羽毛里抓住了一片,自然地表现出某种正确的反应。在这样的注视下,我像被望见了很深的地方。
之后的一个星期,我总是回忆起这晚,只需在幻想中记起黏稠的吻或手指在皮肤上的触感,整个夜晚就重新袭来。我每日如常上班,下班后小睡片刻,醒来后吃饭、洗澡、和钟汶聊天。在规律的生活里,我的幻想不时在溜进时间的间隙。我渴望再一次被钟汶抚慰,尽管我知道了她有女友。
身体像某种开关把我们打开。我无法下定决心与她断绝联系,每次她提出见面我都像被施加咒语般应约。钟汶反复要求互删或是做回朋友,却总是回到原来的状态。
我们开始长时间地聊天,讲尽了自己的感情经历后,就折返回初高中,再走到童年。钟汶谈到影响她人生的两件往事 —— 北方的抗日游行让她误打误撞听了一场关于同性恋的讲座、在学校操场上感受到汶川地震的震感。前者带给她启蒙,而后者怎么影响了她,为何被她视为重要的节点,她还没想明白。
我忽尔无厘头地说起《绿野仙踪》,铁皮人和多萝西一行人上路,前往翡翠国寻找魔法师要为自己要一颗心用来爱人。而魔法师不过是搭热气球降落在奥兹的普通人,却被奥兹国民误以为有无上魔法。最后,魔法师仍答应了这一行人的请求。铁皮人得到了一颗用锯末和丝绸做的心。
魔法师并不懂魔法,戴上绿色眼镜便有翡翠城,心是随手缝制的,但人造的心也会有真的爱吗?
那一晚,钟汶对于自己有女友的事是这样说的:“我有女朋友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本来就说了不跟你谈恋爱。”
“那这件事你女朋友知道吗?”
“不知道啊,我也不怕让她知道啊。我跟你又没发生什么。”
“要是你女朋友知道了,她不会伤心吗?”
“……会吧。”
我陷入的幻想,最终都以钟汶口中说出的 “我有女朋友” 作结,噩梦般令我惊怵。可是我却无法控制自己对她的依恋。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作为哺乳动物的本能,无措地渴求着她,等待她的气味给我解咒。
4.
“我不断堕进空烧的欲火”
我们一起逛过公园,在深圳和香港走了许多路。那晚我们从规整的洁净的商场走上山路,路边是居民楼和学校,有学生背对着我们沿着围墙爬进学校,操场里有穿着篮球服的学生在练习运球,树木草丛遮蔽,去往公园的路显得弯弯曲曲。公园很幽深,我们一直牵着手,我的心也像融进了树林里。
我计算我们相识的时长,她在女友身边时与我聊天的频率,分析每一次她因出轨而产生的情绪波动,记下她要与我断绝来往时说的每一句 “分手”。我心想,分手的前提是存在着一段关系,这无疑证明了我们比起陌生人或朋友要多出一点。我也在她每次说出分手时从不挽回,用潇洒的姿势应对,希望迎来一个终点。
但身体是不同的。
疫情封禁过后,分开后的我们在广州重逢。我和她5个月没见面,那时的我对肌肤之亲渴求到了极点。结束白天的事务后,我不断堕进空烧的欲火里,在夜里一再召唤出与钟汶的回忆。我持续在网络上寻找对象,结果屡降标准亦屡聊屡败,发现原来随便睡一睡都是难事。
只有身体与身体之间的接触才可把我解救回来。 心底冒出的欲望吞噬着我,犹如湿冷的空气里四周点满了火,踏出一步是入骨的寒意,留在原地是步向烧毁的暖意。“热锅上的蚂蚁”,我想起这个比喻。我的触角已被烧焦,匍匐在热油里不得安宁。
我在夜里无法长时间专注地进行任何事务,只得不断地刷新手机,从 Tinder、豆瓣到探探、微博,找寻一个至少可以聊天的陌生人,在自我解救的进度上填满一格。我渴望回到未知爱欲的时期,留在永恒安稳的伊甸园里。
5.
“但一切的魔法都消失了”
这样过了数个月后,钟汶又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刚与另一位女朋友分手,坐在家中像一个空心人,不想与我发生关系却希望我在白天夜里陪伴她。
每天下班后我急忙打车前往她的住所,一整天处于精神亢奋之中。她在家点好外卖等我到来,晚上与她聊天看电影,那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幸福时刻。一周后是七夕,我买了一束花和一盒糖果,我快乐地望着她,只见她眼睛里只有分手后的忧伤,以及我自己的倒影。我为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多么可悲。我和她之间的相处,好像电影《Her》里的人工智能萨曼莎与西奥多断电一次后再也无法与对方连接,原有的密码都发生错位。
我乞求她与我做,但一切魔法都消失了。钟汶不愿意与我接吻,她不再热烈地渴望着我,我那日日夜夜涓涓在体内流着的欲念干枯了。
我知道,我和钟汶真正结束了。
6.
“于是我意识到这是告别”
我第一次察觉与钟汶的告别,是在疫情开始前的圣诞。
钟汶女友的父母在圣诞节到香港探望,钟汶不想独自过圣诞便来深圳找我。我们吃了烤肉圣诞套餐,流连在酒吧、艺术社区。她告诉我,之前一直在出差的女友这周就要回到香港了。分别的时候,往常她只说拜拜,这次她多说一句 “下次见”。
其后她甚少回复信息。疫情开始后,她与女友回了各自家乡再度异地,钟汶又再找上我。不到一个月,我们又不再聊天。她那时与家乡的另一个前女友复合了。
我在每个夜晚打开微信运动对比钟汶每天、每个小时的步数,每日查看数次她社交账号上的关注者与粉丝,猜测她是否找上了别人。有一次,instagram 出错,她的粉丝个数增添了一个,列表里却没有任何我陌生的账号。我连续数日把她列表里所有的用户名截图用以一一对照。
过了两个月,她在朋友圈发了新女友的照片。
疫情后我和钟汶见了一面。她坦露,一开始认识我只感到刺激。我问她我们分开后有没有像现在一样痛苦。她答,“没有感觉,之前我们的关系也只有肉体啊。”
—— 但怎么可能。我们说过的往事,我们走过的每一条马路,我每个痛苦地看着手机的夜晚……都只关乎肉体呢?
我持续与钟汶争吵,但到了第二天,我会再度和睦与她对话,给她分享楼下树荫里的天色。钟汶令我太痛苦了,于是所以,只有钟汶在我身边才能让我快乐。如果她能爱着那么多个女朋友,为什么不能分一点爱给我呢?
我在信笺上写过四个大字 “寻求圣杯”,练废了许多张纸,煞有其事地放在信封里想要送给钟汶。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九莉对邵之雍的爱:
“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界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往往是骑士与主公的夫人之间的,形式化得连主公都不干涉。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当然她没对他说什么中世纪的话,但是他后来信上也说 ‘寻求圣杯’。”
再见钟汶的时候,我又不想送出去了。自始至终,这是我一个人投入的爱,是即使没有爱我仍固执认为爱存在,是即使亲眼看见已经消失却拒绝相信眼见为实的爱。
7.
“一切结束在开始之前”
时间拨回到五个月以前,我与钟汶初次约会之后。那时的我从事一份名为新媒体编辑实为助理的工作,每天整理资料寄送快递抄送文件,在总部和分部之间、上司与领导之间回旋。
上班时我在电脑看到信息亮起的红点,会快乐地点开看看内容,再特意隔一个多小时才回复。当钟汶怒气满满地问 “怎么不回复我” ,我就更快乐了。
经历过对 A 高烧般的爱恋,我需要感到被重视,展现在感情中的游刃有余,不再有应对时的失控,安扎我这段时期对于爱情的学习和进步。我自觉对钟汶的感觉在可控范围内。我不会轻易被对方驯服。我们即将在一场名为爱慕的关系里起舞。
这一次,我原以为会有所不同。
// 作者:仲侣
// 编辑:赵四
// 设计:冬甩
// 头图: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
BIE别的女孩致力于呈现一切女性视角的探索,支持女性/酷儿艺术家创作,为所有女性主义创作者搭建自由展示的平台,一起书写 HERstory。
我们相信智识,推崇创造,鼓励质疑,以独立的思考、先锋的态度与多元的性别观点,为每一位别的女孩带来灵感、智慧与勇气
公众号/微博/小红书:BIE别的女孩
BIE GIRLS is a sub-community of BIE Biede that covers gender-related content, aiming to explore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emales. Topics in this community range from self-growt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gender cognition, all the way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art. We believe in wisdom, advocate creativity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question reality. We work to bring inspiration, wisdom and courage to every BIE girl via independent thinking, a pioneering attitude and diversified views on gender.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